只想对一朵花微笑——略谈黄易的天道观-共3页-第1页
“天道”二字是黄易作品里至为重要的一个概念,也是黄易的主人公追求的最终极的目标,黄易的“天道”来自于中国传统,却又带入了现代人的眼光,与传统 哲学中对天道的见解,颇有相发明之处,伽达默尔所谓“视域交融”,此之谓也。今且略点检黄易天道观的概念与传统哲学上天道观概念的些许同异。天道本自面向 于每个人的自心,各人眼见不同,心悟不同,众生可缘四万八千法门见佛,实无殊胜高下之分,小子强自为文,不外博诸君一哂,错误疏漏处,诸君不访贻之以板 砖:)
一、死
天道听之玄而又玄,实则其根源不出于十丈红尘之中。人生而有限,生老病死,是人无法回避的课题。自人类的思感成熟到可以由眼前扩展至过去未来时,对死亡的恐惧也便如影随形。所有的哲学,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:在必死的境遇下,人生的意义由何而立?
或许这个问题有许多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,但却只能是属于自己的。道可道,非常道,思想受限于语言,而每个人各自的答案也各各不同,关于这一个答案,正如佛陀的开示:“不可说,一说便是错!”
是以,这个问题,留给了宗教,留给道。吴州先生在他的《中国宗教学概论》说得好:“宗教,是围绕生与死的辩证法展开的!”面对生死之际那思维与语言不得 不止步于前的玄冥晦暗之境,唯一可凭恃的,惟有本心。而天道所有的秘密,亦不外是教导世人,要如何坦荡地生,又如何无畏地死……
在中国文化,真正追寻道的人,从不讳言死亡。死亡在他们的眼中,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他们以各自玄妙的道,将令所有人充满未知恐惧的死亡,化成了难以言喻的美。
这个传统,源自于庄子,大成于禅宗。
庄子嘻戏着自己的死亡。庄子将死,弟子欲厚葬之。庄子曰:“吾以天地为棺椁,以日月为连璧,星辰为珠玑,万物为赍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?何以加此!”弟子曰:“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。 ”庄子曰:“在上为乌鸢食,在下为蝼蚁食,夺彼与此,何其偏也?”
而禅师更是有意将自己的死亡当成一场嘻戏。五台隐峰禅师,于金刚窟前将示灭,先问众曰:“诸方迁化,坐去卧去,吾尝见之,还有立化也无?”曰:“有。”师曰:“还有倒立者否?”曰:“未尝见有。”师乃倒立而化,亭亭然其衣顺体。
黄易的《覆雨翻云》,承接了这般死亡的意趣。厉若海死得壮美,封寒死得凄厉,烈震北死得玄妙,而言静庵的死,更是几乎可视为禅门的一段公案。
宽广的长方大殿延展眼前,殿尽处是个盘膝而坐,手作莲花法印,高达两丈的大石佛。殿心处放了一张石床,言静庵白衣如雪,寂然默然地躺在石床上,头向着石佛。
问天尼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道:“言斋主在七天前过世,死前她坚信你会在十天内回来,所以下令等你回来,见她最后一面,才火化撒灰于后山‘赏雨亭’的四周,现在你终于到了。”
靳冰云神情出奇地平静,眼神丝毫不乱,缓缓抬头,望向问天尼了无尘痕的脸孔。
问天尼在怀里掏出封信,道:“言斋主有三封遗书,一封给你,一封给你从未见过的师妹,最后一封是给庞斑的。”
信递过去。
勒冰云接过信,按在胸前,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
问天尼向后退三步,恭身道:“靳斋主,请受问天代斋内各人一礼。”
靳冰云像完全听不到她的话,完全不知自己已成了武林两大圣地之一的领袖,幽灵般从地上移动起来,移到言静庵只像安睡了的遗体前,细审言静庵清白的遗容。
言静庵出奇地从容安祥,嘴角犹似挂着一丝笑意。
她怎会死了!
但这却是眼前残酷的现实。
问天尼的声音再次响起道:“斋主你为何不拆信一看,难道不想知道先斋主临终的遗言吗!”
靳冰云望向问天尼,犹挂泪珠的俏脸绽出一个凄美至使人心碎的笑容,轻轻道:“什么信?”
在言静庵那里,死亡不再是终结,而是一把通向未来的钥匙。她用它,来打开自己徒弟的心。
她是独对空山灵雨时纤弱娇小的女子。
她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圆成上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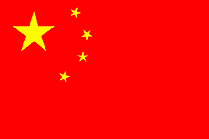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